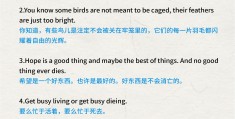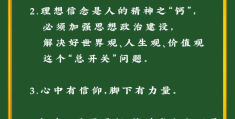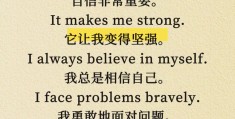信仰与信念区别是什么(信仰和信念一样吗)
《波士顿评论》:
宗教至上还是世俗主义?
导言:宗教是一个古老却又饱受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在宗教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一方面倡导着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却又提防着宗教势力渗透政坛,提倡“政教分离”。这一矛盾现象不禁引发了詹姆斯·查普尔的思考:什么是宗教?与之相对的世俗主义又究竟是什么?宗教与世俗主义之争的焦点何在?本期的法意编译将会探寻宗教主义与世俗主义的起源、含义和冲突,并阐释学者们对此的主要观点,引领读者对此进行批判性地深入思考,力图打破新逻辑与旧制度之间的藩篱。
一、世俗主义和宗教主义的起源
美国公共领域中也不乏许多宗教专家。叙利亚难民危机期间,专家提醒我们,基督教是欢迎难民的。事实证明,许多人都非常熟悉伊斯兰教,他们虔诚地认为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而这些想法通常来自于那些不信这些教派或是任何其他教派的人:有时这些人还会被贬称为“虚伪的政治干预者”,他们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可以实现愿望。如果这些对于冗长复杂的宗教传统的浅显描述是真实的,那么在公众视野中,古老的宗教问题便可以很快烟消云散。和平与难民援助是个世俗上进的目标,如果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长久以来都支持世俗进步主义的教派恰好都支持同样的事情,这将会很便利。但世界不会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我们想从宗教里获得什么呢?
保守的信教人士有着一以贯之的美德:从这点来看,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即使基督教以慈善的名义容忍着其他宗教派别的存续,这些派别也无法超越基督教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进步派人士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徘徊于矛盾和变动不居的立场中。 一方面,宗教看起来很荒谬,但另一方面,理查德·道金斯的胜利无神论也显得很尴尬。当金·戴维斯等人强迫我们面对法律和信仰的难题时,我们常会回以不满的嘲弄,不明白为什么个人良知违背了政治权威就是错误的。古老的马克思主义也将宗教描述为“人民的鸦片”,这一描述蕴含传统智慧,传福音的选民坚持枪支和宗教,因为他们无法分得真正的经济利益。这些试图回避宗教角色的尝试是危险但又可以理解的。伟大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经感慨道,宗教是一个谈话终结者:如果有人声称是出于宗教原因行事,还有什么说的?如果罗蒂今天还在世,他会知道,如果我们避开宗教的问题不谈,我们就会为此纷争不断。
二、宗教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近况
几十年来,有关持续不断的宗教暴力和歧视的研究主要被外包给社会科学家,他们告诉我们,宗教将完全消失或随着社会工业化而私有化。由于这些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构建蓝图。在过去的一年里,市面上出版了一些书籍来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困境:他们问,在民主社会中哪里才是适当的宗教场所? 如果人们对宇宙的本质有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理解,他们如何能够共同生活?
一个答案是简单地直接宣布没有这样的地方。这根本不是一个新地方,但以前试图以这种方式管辖这片公共领域已被证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和智力上都是没用的。政治理论家卡罗·因维尼齐·阿奇蒂的热卖新书《相对论和宗教:为什么民主社会不需要绝对道德》(Relativism and Religion: Why Democratic Societies Do Not Need Moral Absolutes)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新方法。阿奇蒂不是在以世俗理性角度的道德或民主合法性的名义简单地驳斥宗教。他不会试图证明金·戴维斯是错的,或是解释为什么婚姻法应该是世俗的。相反,他认为只有复兴的哲学相对主义可以使我们摆脱长久以来的宗教束缚。他非常重视宗教论证,并在书中用很大篇幅耐心地重构了罗马天主教中反对相对论的观点。他认为宗教对相对主义的批评是错误的,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声称,对相对论的世俗批评也是错误的。

如果没有了“宗教”,世俗主义会因此失去相对应的概念,这时会怎样?
阿奇蒂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天主教和世俗的民主理论家间尽管有着诸多不同,但都同意一个基本观点,即伦理相对主义对民主而言是个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一直在强调这一理念,而天主教教条,像大多数美国政治家所宣称的那样,认为民主国家必须以强大的宗教价值基础为支撑。世俗的民主理论家,如于尔根·哈贝马斯和约翰·罗尔斯当然不同意,但他们接受一个基本前提,即相对主义是一个问题,而民主国家必须有一些手段来判断什么是真理。在神学领域,他们用不同形式的新康德哲学从纯推理中得出民主的道德。
阿奇蒂回应说,这个问题一直处理的不好。如果相对主义是民主和意识形态确定性的先决条件,那么宗教或世俗是否真的面临威胁?他的案例完全建立在一个世纪前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克尔森提出的类似论点上。从本质上说,阿奇蒂认为,进入民主辩论有一个前提:我们都必须同意我们的承诺是“相对的”。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变得冷漠或是放弃我们的价值观。然而,这的确意味着,我们不应抱着这样一种先入之见进入公共领域,即认为我们自己对真理的看法才是唯一有效的,并应获得法律的支持。
阿奇蒂在书中的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在实践中它会是什么样子?阿奇蒂最终只是简单地想要从民主中消除宗教社会。他认为,“民主只有在一个全是民主派的社会中才会真发挥作用。”在他看来,现在的社会是相对主义者的社会。但是当一个信奉宗教的演员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宗教信仰是相对的后,在这样强烈的意识支配下他还能当一个信奉宗教的演员吗?在有关生命存在的问题上,如果我的宗教信仰是认为和平主义或堕胎管制是相对的,这是什么意思?这种相对是与什么相对?如果我们让金·戴维斯接受了她对上帝的信仰是相对的,因此不能合法的对他人施加限制,我们就是在粗暴地让她颠覆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假设可以说服宗教群体接受双重意识,这时阿奇蒂的逻辑才有意义。最终,阿奇蒂的那种相对主义看起来有点像教条主义。
这也不一定是个问题。在这个宽容、文化多元且观念不断变化的世界上,阿奇蒂的教条主义令人耳目一新。但当面临具体问题时,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相对主义能够提供何种帮助。我们可能对要求一个坚定的信徒牺牲她的信仰感到不适,但信徒自己却不会因拒绝这样的要求而感到不适。这点在阿奇蒂笔下的英雄——凯尔森的命运中得到了印证。虽然阿奇蒂没有提到这点,但凯尔森自己觉得被宗教极端主义吞噬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精心起草的奥地利宪法却于1934年被一位天主教徒独裁者恩格尔伯特·道尔斐斯推翻。在面对宗教狂热者时,相对论溃不成军。
正是这一经验事实激发了美国人迈克尔·沃尔泽这个激进派人士的兴趣。他为阿奇蒂的论点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实践版本。他想知道如果世俗主义有如此显著的吸引力,纵观历史,为什么它却常常赢不了?沃尔泽同意阿奇蒂的说法,认为民主派人士太想用对付孩子的方式来对待宗教。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有争议的关于伊斯兰主义的文章中,他提醒进步派人士,世俗主义是遗产中的重要一部分,当他们指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暴力、极端、危险的信念时无需感到痛苦不安。在《解放的悖论》中,沃尔泽扩充了这些观点:他问,为什么这么多高尚的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解放运动都是以宗教极端主义的方式呈现的呢?换种说法,为什么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宗教问题,为什么阿奇蒂的解决方案不起作用?
沃尔泽说法的一个优点是,他提醒我们,世俗主义浪潮有望席卷阿尔及利亚,印度和以色列等地,并会因此提供研究案例。瓦尔泽声称,虽然这三个地方目前都经历着宗教极端主义的痛苦,但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俗、民主甚至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知道他的模型在某些情况最适合这样的案例;这本著作中的案例十分精彩。)这些运动都由受过教育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往往非常熟悉西方世俗传统的大都市。在解放运动的幸福景象中,现代化精英和群众(尤其是来自农村和信仰宗教的群众)间的结盟变得有可能了。但是当宗教解放让位于宗教管制,现代化精英和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冲突也会变得愈加明显,宗教信仰又开始变得有相对性了。
如果阿奇蒂打着世俗主义的旗号试图全然诋毁宗教,沃尔泽看不出这能比恐怖袭击或是性别压迫多些什么进步意义。他驳斥了信教公民可以被说服的不那么信教的说法:在他看来,这样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沃尔泽认为,世俗主义者应该学会批判性地接触宗教传统,以便了解那些古老复杂的信仰的进步性和世俗性。相比于过去的将宗教作为传统糟粕并对其在文明社会中的地位加以排斥,我们应该保留这些宗教,并尝试培养可与世俗相融的宗教形式。他指出,在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传统中有女权主义这方面的资源,而西方女权主义者如果学习这些可能比用世俗主义的方法更能获得成功。
沃尔泽的观点当然很有吸引力,其中有些论点还可能是许多进步论者的常识。他们一方面警惕对无神论的吹捧;另一方面,又想追随自己内心有关性别和平等的看法。这个观点给予宗教巨大的解释权力,同时也说明宗教可以改革,而且或许比政治经济的深层结构更容易改革。人们常认为宗教是最终的解释变量:是恐怖袭击乃至战争的原因,是投票模式和性别政治的来源。因此,宗教需要管理。沃尔泽和阿奇蒂二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管理宗教的方式,想从世俗的角度定义什么是被允许的宗教。如果说阿奇蒂想完全回避宗教,沃尔泽则想要将它用于世俗目的。然而,宗教继续存在,他希望进步论者至少可以将宗教传统的某些方面培养成迈克尔·沃尔泽可以接受的样子。这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还只是个止损措施?《自由的悖论》并未铺设一条前进道路,而更像是一个沮丧的左派人士的挽歌。沃尔泽悲伤地承认:“辩证法似乎并不像过去那样有用了。”他的目标是将宗教作为一个火花塞,直接启动那辆老摩托,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新的理论类别。
三、宗教主义与社会政治理论
宗教的持续性使我们对政治和社会理论有了更根本的重新思考。当面对看似无法解决的困境时,第一个步骤可能是要阐明我们的立场。如果没有“宗教”这样的东西,因此没有了可监管的现象时该怎么办?事实要比听起来的更复杂。当然,有些官方认可和实际存在的形式可以明确指代一种超验的神性,这时就要有术语来描述这样的现象。但当该术语指代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存在抑或是一场战争时,这个概念就会崩塌。当知识分子把宗教当成是个要解决的大问题时他们认可了这个原初概念,最终矛盾地赋予了它以权力。当我们声称有两种难民——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难民时,当我们声称有两种民族解放运动:世俗运动和宗教运动时;当我们声称有两种话语:世俗言论和宗教言论时,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开始认识到,世俗主义不是简单的相对主义或进步主义与宗教力量对比下的胜利——正是想象有宗教这种东西的存在,才有可能跨越时空的差别,将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极不相干的实体相联系。思考一下这样的现象: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和社会关系都被归类为“宗教”,如恐怖主义、主日学乃至选举政治。令人费解的是不知道这些现象究竟有何共同点,而更令人困惑的是如何将它们与国歌或商场里的圣诞老人相区别。
宗教自由的概念使我们认识到:生活和社会中的事物可以被区分,有的可称为宗教,而有的不是。
这种认为宗教的本质理念可以存在于不同社会中,因而可以被分析和区分的想法大约出现在三个世纪前。欧洲传教士和帝国主义者提出了这一想法。但在纷繁多扰的世界中,这一想法的传承并没有增强人们的信心,也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来支撑这一想法。对宗教种类的解构看起来像一个学术沙龙游戏,但实际上赌注很高。将宗教作为解释变量和突发事件的起因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并以此建构了一个强大且毋庸置疑的世界观。
四、宗教与世俗之争的未来趋向
世俗主义者,甚至一些宗教人士,一般认为宗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世俗主义可能是个更大的谜团。在新出的两本书中,政治科学家伊丽莎白?沙克曼?赫德和人类学家萨巴?马哈茂德通过宗教自由这一典型的政治承诺来研究世俗主义,而这种具体的研究方式值得称赞。世俗国家不会根除宗教,而是尊重每个人的宗教权利,构造宗教多元社会。这个想法听起来毋庸置疑,但当我们仔细看看它在实践中的应用时,会发现宗教自由的辩护者如贝克基金支持者或热忱的无神论者都不会这么做。正如赫德和马哈茂德所认识到的,如果我们宣布某物是自由的,我们会假定那东西是存在的。因此,宗教自由的概念基于我们认为生活和社会可以分裂成碎片,其中有些可以被称为宗教和其他的则不能。这种姿态对于沃尔泽和阿奇蒂的管理策略以及那些宣布长期支持宗教自由的自由主义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但是,与大多数管理策略一样,这种策略可能很快滋生暴力。
赫德在《超越宗教自由》一书中探讨了世俗主义和宗教自由的影响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 政治世俗主义以及与之相连的宗教自由的逻辑,长期以来都是美国、联合国和许多独立国家治理的核心。 她认为给宗教分类是很笨拙的做法,宗教——世俗二者间的界限比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要更为模糊。 她认为,无法将社会中的宗教元素和其他元素完全分离开。她声称:“基于政策目的对宗教行为进行分类,是在假定某种形式的由宗教引发的行为不仅逻辑上不贯通而且也是反社会的。”
《超越宗教自由》引用了世界各地的例子来详述宗教分类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宗教已经成为了社会控制的对象,并由国际宗教自由美国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监督,而该委员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同行。赫德认为将消灭宗教视为治理的一个重点,是在努力 “维持和扩大特定形式的宗教和世俗差异,掩盖其他造成社会紧张和冲突的因素,延续历史上对宗教、宗教主体性以及自由本身的具体理解。”确认公民身份时需要优先考虑宗教,而国家机构也正是通过创造这些差别来进行治理。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笨拙逻辑想将这些不断变动着的宗教神话为“有显著领导者和明确分界的神圣信仰群体”,而不是对现实的反映。
赫德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在这场宗教和世俗的古老战斗中,必须结合复杂的地方战略政治斗争中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而不是把它们作为相互竞争的对手。马哈茂德在《世俗年代的宗教差异》一书中,以人类学家的视角从生活经验和地方影响出发,进行了这样的研究。基于一年多的在埃及的实地调查,这本书展现了当代埃及中的个人和群体如何运用这些概念,并最终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马哈茂德和赫德一样相信,承认世俗主义的必然先决条件是将对宗教的确认和管理作为个人身份的核心。她认为,“世俗主义下的宗教管制,并不是简单地调整了它的权力而是改变了它,使它对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身份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通过对科普特人和巴哈伊人的探索,马哈茂德阐释了这两个少数群体是如何选择性地采用了“宗教少数群体”这样的身份,使得其非埃及人的身份变得更为显著,以便基于埃及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条款提出某些法律请求。
也许马哈茂德的讨论中最有趣的一点是监管性别。这也是沃尔泽观点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沃尔泽认为世俗主义主要基于对妇女权利的信仰,而这点经常被传统的宗教社群所忽视。但马哈茂德所展现出的世俗主义的逻辑可能恶化这个问题,因为他的逻辑将公共和私人领域分裂开来。根据这个区分,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家或宗教场所,我可以相信任何我喜欢的愚蠢的事情。只要我没有用子弹逼着别人去改变信仰,我就没有犯规。但这被认为是对宗教当局的屈服。世俗主义不只是制造无谓的分裂:它确认了宗教在家庭中的合法地位,并因此确认了家庭和性别关系。因此,世俗主义可能加强了宗教和女性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切断它们。
事实证明,世俗主义至少是造成持续的宗教分裂和宗教冲突的部分原因,因此很明显不会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回到我们开始时的例子——有人声称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还有些善良的世俗主义者经常暗中将独立现实的东西称为伊斯兰教——有了它,对手就可以挑起战争或是将某些人当成是威胁。
认识到世俗主义可能引发冲突为阿奇蒂和沃尔泽提供了一条政治神学路径。然而最后赫德和马哈茂德工作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他们留给读者们一些严肃的问题,如一旦不稳定的宗教和世俗二分法结束后又将留下些什么。当我们秉持阿奇蒂的民主演讲规范、沃尔泽的性别平等和国民自由,以及传统的国家是社会进步最重要代表的观念时,我们如何想象一个“后世俗”的情形?这可能吗?
无论是学者还是公民都将会遇到这些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除了在有线新闻工作室中被热烈讨论外,还在线下激发了有关宗教的真正讨论。我希望能在关注长期被贴上“世俗”标签的观念的同时,批判性地思考这样的分类。然而,我们必须从宏伟的宗教或世俗运动叙事中剖析出具体问题。宗教和世俗主义之间的冲突就像我们目前的许多战争一样永无止境。解决方法永远不是派遣更多的部队进入战斗,而是停止战争。抽象的审查宗教只会分散注意力——那些在传统中被称为宗教的东西由于特定原因而被特定的人操控。宗教和政治一样,从根本上来说是地方性的。因此,要理解它的种种表现不能单凭抽象的想象,还要靠对特定个体和事物感知。而这样的感知源于最古老的民主美德——智慧、同情心、信仰。
姜宛如翻译
出处:
JAMES G. CHAPPEL, Holy Wars, Secularism and the invention of religion, Boston Review, April 25, 2016 LITERATURE & CULTURE.
网址来源:
https://bostonreview.net/books-ideas/james-chappel-secularism-religion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王咪
发布于 2025-07-02 22: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