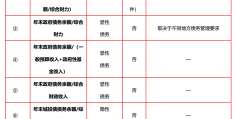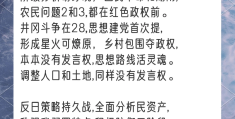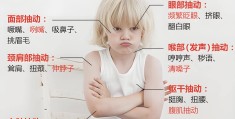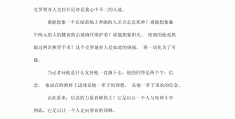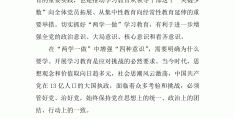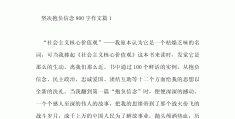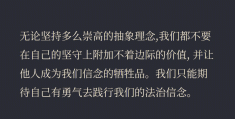信仰一旦崩塌是什么歌(信仰崩塌了)
声明:我们是澎湃新闻“有戏”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没有栏目官方微博,唯一的APP叫“澎湃新闻”。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有戏”栏目,未经授权,谢绝转载。转发朋友圈请随意。
撰文:阿水
《曾经》(Once)和《再次出发》(Start Again)的导演约翰·卡尼(John Carney)又有新作交出,这部《初恋这首情歌》(Sing Street)可视作“音乐三部曲”之尾声。
从纽约回到他的故乡都柏林,再回到愁云惨淡又一身反骨的青春时代,约翰·卡尼言明这部作品和之前的两部非常不同,“是最诚实的一部”。
当然,青春时代的卡尼并非影片中家道中落又魅力四射的主唱原型。事实上,当年的卡尼远没有这样醒目,黯淡的身躯里却同样跳动一颗永远不羁永远叛逆的爱尔兰之心。
“Fighting Irish, Drunk Irish, Melancholic Irish”,外人眼中的爱尔兰特质是这部电影的底色。尾声处,主唱康纳(福迪亚·瓦尔什-匹罗饰)在寥落的舞台上排演,随歌声学校礼堂逐渐光华灿烂,他爱的人一一出现,成就一幅他梦想中美国高中舞会的无忧场景。
这场景令很多人误以为影片有个快乐的结尾,其实不然。导演卡尼一把年纪了还是这样的直脾气,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早知会这样被人误解,不如让男女主角在结尾时死了算了。”
真实的结尾中,15岁的康纳和16岁的拉菲娜(露西·宝通饰)在康纳的大哥布兰顿(杰克·莱诺饰)的帮助下驾祖父的小艇去往一海之隔的英国,瓢泼大雨中自诩为“未来主义者”的康纳和拉菲娜用笑容一扫阴霾,将与无数远离故土的爱尔兰人一样怀抱乡愁闯荡世界。
他们不得不走,因为“但凡流着艺术血液的人,留在爱尔兰将不是疯了就是成为酒鬼”。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爱尔兰在卡尼的镜头中宁静优雅而死气沉沉。每个少年角色几乎都来自不幸的家庭,或是父母不睦,或是破产,或是单亲,或是父母是瘾君子、精神病人。
有一幕,康纳和大哥布兰顿坐在楼梯上看着他们的母亲(玛利亚·多耶·肯尼迪饰)以度假的姿势坐在门口晒太阳。“当太阳被树遮挡,她就会回来。她一直希望父亲能带她去西班牙度假。”
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现实荒唐又残破,只能在短暂的一刻里逃避现实沐浴在阳光中,假装自己在西班牙或者其它更好的别处。
爱尔兰人的忧郁和酗酒不知孰先孰后,他们的硬骨头与反抗史亦不知孰先孰后。但是在影片中故事发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爱尔兰特质早已经俱全。
又因为都柏林的保守和一成不变,所有这一切都站在青春的反面令人窒息。
在成人世界的阴影里长大的孩子们拥有共通的特质,他们敏锐叛逆,时刻想要逃离。
康纳如此,在他眼中一切皆完美、眼波如云开月出般流转的拉菲娜如此,乐队的每位成员皆是如此。“你去伦敦吧,如果能拿到一纸唱片约再回来接我们。”
两代人之间,又因布兰顿未竟的逃离之路而凭添宿命的味道。
得知父母二人终于决定分居(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不准离婚),平时一贯以调笑逃避的方式应对二人争吵的布兰顿真的伤了心。和康纳二人坐在房间时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康纳:你怎么了?
布兰顿:我不知道,只是现在有点焦躁。
康纳:为什么?
布兰顿:因为我两天没飞叶子了。
康纳:为什么?
布兰顿:因为我想为自己的人生做点正经事。
康纳:为什么?
兄弟之间即便可以结成对抗糟糕父母关系的同盟,彼此之间的隔阂之深却依然叫人心酸。
之后布兰顿终于发飙:“你只是走在我的老路上,我才是那个拓荒者!”

他也曾是学校的200米冠军,是技术极佳的吉他手,如今却成为颓废于家中的嗑药废柴青年(还仅仅21岁)。
一个康纳的出走,背后大约有千万个在家乡沉沦的布兰顿。他们是出走者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的音乐和人生导师。
康纳出走前,布兰顿曾告诉过他爱是什么:爱是悲欣交加(Happy-sad)。
不可能是纯粹的欢欣,必然会有痛苦,就好像好运和歹运总是相生,爱也是复杂又轮回的东西。
为了让弟弟更加理解什么是“happy-sad”,他拿出一张碟——The Cure的《The Head On The Door》。
这张“The Cure”1985年的专辑是乐队的转型之作。此时的他们开始探索电子舞曲的跳跃激爽,又加入异域元素;有时候又纯真得要命,一首《The Blood》的急速扫弦前奏与影片中的《The Riddle Of The Model》神似,提神醒脑,又暗藏玄机。
在音乐上,这部影片与此前的《Once》和《Start Again》有了很大的改变。
尽管影片的基调未变,皆有关对个体身份的认同、去乡的离愁、骨子里的反叛和与生俱来对音乐的热爱,《Sing Street》却更勇敢抱定“未来主义者”的信仰。
这群孩子没有信仰,但是相信未来,相信旧的应该腐朽,新的必须被诞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做全然不同以往的音乐,但至少这一次的音乐不再似前一部一把吉他加一个人声这样朴素。
除了The Cure,影片中提到或出现音乐作品的还有Duran Duran,Joy Division,Motörhead,The Jam,Michael Jackson,A-Ha等(因为版权昂贵的问题,剧组的很多设想并未实现)。
复古又摩登,前卫又优美,这些家伙是美好1980年代的缩影。在这些音乐“滋养”下的康纳和他的乐队伙伴们(实际作曲家是Gary Clark)做出来的音乐像一部Brit Pop小史。
以导演最爱的《Drive It Like You Stole It》和《To Find You》为例,前者青春恣肆地快要飞上天,后者一架钢琴一曲悲歌,“我不相信命运,但是你对我发誓的每字每句,都让我的信仰开始崩塌”。

但是很奇怪,这些音乐都要结合影片才能百分百发挥“功效”,而不似前两部(尤其是首部《Once》的原声)耐得住反复聆听。这大约也是“未来主义”的特色,如影片中布兰顿、康纳兄弟俩痴迷于的音乐录影带,必须画面与音乐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最后说一个花絮:导演卡尼曾在宣传期表示上一部《Start Again》的女主角凯拉·奈特莉总是在隐藏自己,又因为是大明星,拍戏总有一群人围着挺烦的,以后还是希望与专业音乐人合作。尽管此后他又为此道歉,但多少也是大实话。
因此狷介又自傲的卡尼才总是让人期待,至少他的电影里依然保有纯粹和手工气息。而永远的爱尔兰愁雾,又何尝不能打动所有人。
发布于 2024-12-10 00:12:21